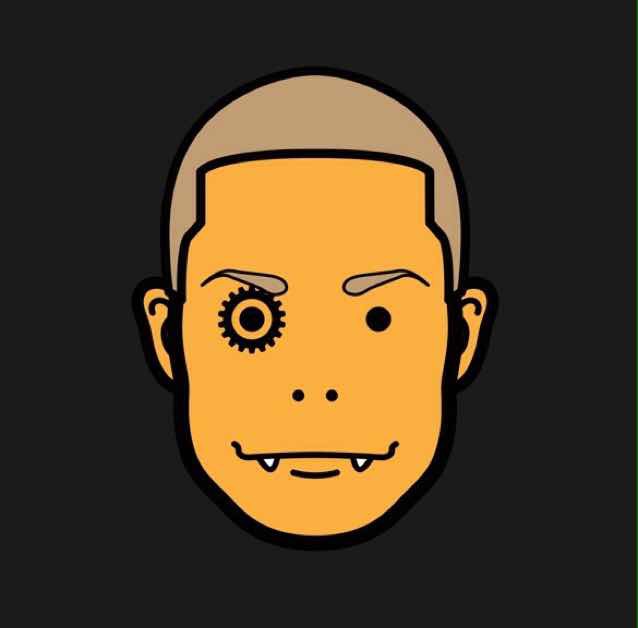贫民窟也不过如此
初中时期的某一天,同学在我家玩,我把地图平铺在地上,趴在上面,屁股撅的老高,当手指滑动到右下角的时候,突然宣布:我一定要去这里看看,因为这里有全世界著名的贫民窟!
同学说:“你疯了!一定是FIFA2000玩多了。”
母亲说:“好,先把衣服穿上,一会儿先帮我买袋盐去啊。”
姥姥说:“那比上海还远,过去一趟多麻烦啊。”姥姥去过最远的城市是上海,解放前在那里生活过2、3年。
我当时手指有点偏差,按在了亚马逊雨林里。
十多年以后,我和好友Pietro站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长途车站前的过街天桥上,脚下是川流不息的轿车,路的两旁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一侧背靠着山,一侧背依着现代化的城市中心。我们要去向有山的那边,那山上错落着的五彩缤纷的简陋建筑,就是真正的贫民窟。

瘦骨嶙峋的男孩正背着一个大木箱子艰难的爬上天桥,找了一个不碍事的角落坐下来,快速熟练的支起摊子,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香烟,价格低廉。他低着头,并不叫卖,似乎只是等着来回经过的路人施舍给他几块钱,他好用香烟作为回报。
“阿喽,阿喽!”一名乞讨的年轻人带着恶臭的气味从对面过来,不知道他已经在这大街上流浪了多久,他是一个健康的人,站直了起码有1米80的身高,黑色皮肤更加衬托出健美的身材,也许只是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这里,根本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他们是与贝洛奥里藏特的朝阳一起迎接我们的人,犹如这座城市。
大概10个小时之前,我和Pietro从圣保罗坐上长途大巴,汽车摇摇晃晃,十几分钟就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到贝洛奥里藏特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正好省去一晚住宿,这对于经费并不富裕的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巴西国内的城际交通主要是飞机和长途汽车,火车很少,尽管偶尔有长途巴士被劫持事件发生,但这种方式依旧是最经济性价比最高的出行方式。
抵达目的地之后,长途车站周围的环境除建筑风格以外,与中国一些小县城无太大差异,小商贩、流浪汉,到处都是脏乱差。贝洛有一条地铁线,差不多成S型,一共也没有几站地,地铁应该就是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贫民窟分散在城市周边,离地铁越远,也就越贫穷,越杂乱无章。由于酒店距离大巴车站也就2公里的距离,我们决定步行过去,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城市。
P君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摄影题材,他把沉重的背包卸下来放在地上,打算就地冒险换镜头,他让我放风:“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盯着咱们。”我回答:“放心吧,周围没有人不盯着咱们。”
我们蹑手蹑脚的走在大街上,因为长相太“东方”,行为太古怪,身边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好奇的从上到下打量着我们,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这倒让我想起08年奥运会之前,我的大学旁边正有一座建筑工地,午休的时候农民工在街道边马路牙子上排排坐,偶然从他们身前经过一位超短裙美女,他们全部抬起头,捧着手里的碗筷,停止咀嚼,认真的看。这次轮到我们被围观,难免让人有些不自在,更不同的是,我们不了解这一地区人们的性格,也猜不出谁在想什么,哪一个心中会起歹心,哪一个会突然把我们叫住。
“chineses people! my best friend!”一口发音烂到极点的英文从路边停靠的中巴里嘶喊出来,那巴士像是阿联酋的劳工车,不知开了多少年,车皮上的漆都快掉光了,一个黑皮肤的老兄正推开老式推拉的车窗,探出整个上半身,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冲我们憨笑,整个车里的也都咧着嘴笑开来,黑色的面孔只露出洁白的牙齿,小巴士被他们搞的一晃一晃的,车震那般。然而他们其实并没有旁人想象的友好,只是在无聊中自己找个乐子罢了。我只想赶快摆脱他们,他们越是发狂的笑,我心中越是忐忑不安。
我们一直在大路上走,旁边延伸出来的小道虽然近,但是不安全。当我们抵达酒店的时候,时间已经距我们下车时过去了1个小时,荷枪实弹的安保在酒店门口巡逻,提醒着我们,此地不宜久留。

我和P君决定去贫民窟的时候,没有向导的带领,我们只是想碰碰运气,看看贫民窟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总觉得,那些持枪抢劫绑票杀人的事情只是小概率事件,并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话虽如此,大脑里也是经过一番纠结和思想斗争的,因为在那种地方,你走在路上会有一种条件反射,人类的本能会告诉你哪里安全,哪里有潜在危险。
我们在谷歌地图上查询了贫民窟的路线,知道军警的位置,又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放到酒店,只带着手机,出发了。漂亮的贫民窟挨家挨户把外墙粉刷的五颜六色,乍一看就是搬到山上的威尼斯彩色岛,但走进之后你就发现,墙皮到处是裂缝,个别地方还有子弹打进去的弹孔。村口屎尿垃圾一地,臭气熏天,某些角落还散落着碎酒瓶子,不知是哪个醉汉彻夜未归,在路边撒酒疯。几个人行为乖戾的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在路口侃大山。
从酒店到贫民窟,只相隔一座天桥。桥上的流浪汉像尸体一样,倒在并不宽敞的人行道上,他们一般会一直睡到中午,路过的时候,极其小心才不会碰到他,对于一穷二白的人,或许你吵醒他,他便会要你的命,这完全看他心情了,天知道他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抵达村口,凶恶的犬吠声率先沸腾着冲出来,最靠前一排的房子上,有人开始吹口哨,没有曲调,是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出来的效果,更像是向村民发出某种暗号——有不明人物到来,非法交易的人们注意了!我们只听到声音,看不到吹口哨这人在哪。再往里走,我试着掏出手机拍照,果然,一下子围上来6、7个人,他们之中有男有女,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葡语,面目狰狞,像是要吃掉我们。
一丝冷意穿过近30摄氏度的空气,席卷了我的全身。“妈的,这贫民窟够刺激,肾上腺素已经开始分泌了。”我心想,有点看恐怖片撞上鬼的感觉。一群人叽叽喳喳,一个妇女想拉住我,但很快被我挣脱开,我道歉着向后退,保证只让他们出现在我的身前,与此同时依旧面带微笑,证明我并无敌意,微笑也许可以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
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只不过是想让我们交点钱,为我们做向导,带我们在贫民窟里走一圈,由于太渴望赚钱,所以拼命争取,像食肉动物争夺猎物一样。
“你看,我们身上没带钱,等我们回酒店去拿钱再过来好么?”朋友用英语夹杂着葡萄牙语说道。再过来?还哪敢,先逃跑再说吧!单纯的村民竟然相信了我们的话,痛快的放我们离开了。

6月份的巴西,下午4点多天就渐渐暗了,我们每天必须控制在下午4点左右回到酒店,再晚的话,一是不安全,二是这个酒店周边几乎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快速公交道路两旁时时刻刻都蹲着社会青年,三三两两,时而低语,时而打闹,他们整天无所事事。白天出来在大街上晃荡,日落回家吃饭看球。
这样的日子让我呆上3天就会厌烦的要命,我们每次路过,都能看见几个17、8岁的男孩儿,他们有时候会靠在街边放风筝打发时间,那风筝应该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一张报纸下面粘两张纸条,运气好的话可以飞个3、40米,大多时候都只是在低空来回打转,几个男孩操纵着手里的鱼线,激烈的叫嚷,亦或是争吵着。
一次我们走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似乎情绪不高,其中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用手里的石块往地上划拉着,另外几个盯着穿梭的车流发呆。
“嘿!”其中一个叫我们。
我看了他们一眼,没有搭腔。
“cigarette(香烟), cigarette。”大个子扔下手里的石头,用食指和中指在嘴边比划着,露出小臂上不知是什么图案的纹身。他的英语水平不高,听上去跟“secret(秘密)”很像,仿佛在说,给我们根烟,我们有神秘的事情告诉你们。
我无奈的摊摊手,示意他们我们没有香烟,让他们失望了,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开了。好在他们并没有追上来,如果他们追上来,我就准备把兜里的2、30雷亚尔留给他们了。
我们沿山路向上爬,酒店就在相对较高的地方,途径的平房全部配备有24小时的监视器、电网或者铁丝网的防盗设施。一辆废旧的汽车没有规矩的摆在路边,玻璃碎了,轮胎也是瘪的,里面的座椅有被烧焦的痕迹。这个地区几乎没人,偶然从拐弯处冒出来的2、3个人,就用诡异的眼神盯着我们,好像跟我们有深仇大恨一样。
走到一处拆掉一半的建筑,在那废墟旁,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正趴在一辆轿车的窗口跟司机嘀咕着什么,见我们路过,他慌乱的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口袋,紧接着,汽车喇叭声不满的响起来。
“抱歉,我们只是路过的游客。”
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知道。
天还没黑,酒店周边的饭店全部大门紧锁,我们走进一家仍在营业的私人便利店,几个警察围坐在并不宽敞的吧台前,享用着廉价的汉堡,有说有笑。柜台里的商品不多,实在是无从挑选。想想两周前我还在家里安逸的吹着空调,吃着外卖来的全家桶套餐,或是出门到马路对面的红莲烤鸭店外带一只烤鸭。每周去东单踢几场球,回来的时候在球场南边的第一个小卖铺买瓶水,雷打不动的坐地铁二号线回家。我偶尔抱怨几句北京拥堵的交通和人满为患的地铁,用针给家中浴室里堵住的喷头挨个“打眼”疏通,自己更换坏掉的灯,不厌其烦的给小猫更换猫砂;我想到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上邻座的乘客一直很大声的嚼口香糖,叫人心神不宁;我又意识到国内马上要到上午了,大家就要工作,总有人在我就要睡着的时候联系我,我手机24小时开机,生怕错过什么;其实自己已经拖欠了太多的稿子,以至于它们越堆越多,我逐渐忘得一干二净,而个别干完活不结款的客户也无休止的拖欠着我的薪水……我变得的不敢随便许诺别人即使可以完成哪些事情,我变得更熟练也更机械,我经历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却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满足,但更愿意苟且偷安的耗过这一阶段。
“呯呯——呯——”三声清脆的声响从马路对面的平民窟传来,像过年时小孩玩的摔炮,由于距离实在不近,所以可以判断,这个声音要比摔炮声大得多。
“天黑以后尽量不要在外面活动。”体态稍显臃肿的警察把最后一口汉堡咽下去后起身跟我们说,他像是其余几个人的领导,刚刚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葡萄牙语。没人告诉我们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他们带上头盔,慢悠悠的跨上摩托,依旧谈笑风生。
显然他们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夕阳在彩色的贫民窟背面落去,晚霞把头顶上的云映的通红,最后把仅存的一点光亮也拽下山去。星星点点从山上平房的窗散射出来,像是苍穹之上银河的倒影。从酒店的房间里看过去,路灯照耀下的蜿蜒山路像是落魄老者西服上的胸针,竭力让自己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品味,以至于赢得一丝让人暂时麻痹的尊重。
我和P君躲在酒店里看球,比赛结束之后,微信朋友圈里又出现大家各自的生活,跑步,早餐,堵车,上班,和昨天一样,按部就班。
我竟然开始有些佩服初中时期宣布要去巴西贫民窟的我,那时候我的确只是说说而已,反正吹牛又不用上税。记得那天我穿好衣服买盐回来,发现店家竟然多找了两块钱,这让我窃喜了一个晚上,因为我的四驱车还差两块钱,就可以装一个“凤尾”了。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真是很容易满足。
光阴荏苒,当时那个说我“疯了”的同学,现在早已没有联系了。
如果姥姥依旧健在,她一定会嘱咐我,到了巴西多穿点,注意安全。因为在她不糊涂的日子里,每次我出门上学,她都这么说。
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现在,我真的很怀念她。
========================================================================
微信公众账号:“寻找旅行家”,每天为你精选一篇有见地的独家专栏文章,欢迎关注,互动有奖^_^

上一篇:旅行路上,我就是一条蝴蝶鱼
下一篇:其实快乐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