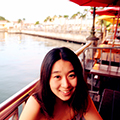欢迎来到安娜普纳基地营
毫无预警地,庞然如实体般坚硬而沉重的爆裂声,从半空中震怒一样的哐当砸落,几乎令四周白幕及脚踩大地随之撼动。白幕是正在迅速累积且遮盖一切的浓雪,以及隐藏其后的、深雪覆盖的谷地与两侧山头。『前方雪崩危险区』脑海中马上闪现那张警告标示,它就位在这条步道的入口,已被积雪反覆压得摇摇欲坠。雪崩!我满脑子这两个字,惊恐之甚,说是吓到魂不附体毫不夸饰,四下张望,觉得想哭,不知在这片令人怀疑自己是否已瞎了眼的纯白中,该往哪里逃。
***
啪嗒。J以为下雨了,抬头一看,加德满都密密麻麻如树丛的电线群上,一只鸽子飞走。他把帽子脱下,正中一坨鸽屎,我笑得尴尬,因为明天我们启程往安纳普纳基地营,喜马拉雅山中,任何异状都使人有不安的联想。不过J本人倒随遇而安,他说,幸亏有帽子,天降黄金,必是好兆头。
日
多数情况下,步行从早上九点开始。

(启程 登山入口)
这段十多天的徒步并不难走。用以通往基地营的步道,实是当地居民往返交通、赶牧牲口的阡陌小径,其中最多数,就是台阶。我们起头便迎来一堂入山震撼教育,开始提步的几小时,是无间断、直上、不见尽头、仿如通往奥林匹斯山的登阶,阶阶陡险,需全神贯注,然而阶阶亦满溢牛羊狗等各式粪便,也不可不逼视,这是山区典型的人文景观。石阶在陡坡顶端的村落稍歇,我们总算确定自己尚未断气,向导拉马说,这块村,在两年前地震发生时,整片山从顶到谷底,连带抹去了大半村,由于事发在深夜,熟睡中的多数居民未能逃出。
同在陡坡,另个村落则可爱且幸运,放眼辟出层叠的荞麦梯田,像翻开篇篇柔软青绿的书页,绿色麦尖与其下的土色田埂,交错一道一道纹理,仿佛绘附着山坡的等高线。若有风吹拂,荞麦梗便晃荡着它们的毛毛虫脑袋,生机奕奕地沐浴在明灿的日光里。一只喜马拉雅小山狗跟着登山客后头走了好长一段路,这里的山狗长相千篇一律,类似小号藏獒,黑色厚毛的脸上点缀两点棕色蛾眉,傻乎乎的样子让人想抱回家。


(山狗)
来了才晓得,二月正逢高山之春,日日有雾,常峰回路转,忽见周遭已花盖满树。我们沿途观察不同海拔的花开,发现花序与花色也跟着攀登而变化,温暖的低处多朱红,但随高度上升,颜色渐转为桃粉。回来后一查,才知那是尼泊尔国花高山杜鹃。我诧异杜鹃竟有乔木品种,却被妈妈嗤之以鼻,“我过去爬山的时候,高山上的杜鹃都长那样。”妈妈年轻时登台湾百岳,她说,玉山上的草原,满山满野铺天盖地的都是怒放的百合,延绵数里,美得不可置信。她还告诫我们,人说山中有魍魉、山魈,登山时千万不能连名带姓的呼叫队友的名字,不然鬼魅便会学舌,趁人心不备时在风中呼喊,诱人脱队,走向悬崖深谷。



(高山之春)
阶梯持续爬升,最后终止在山的棱线,这里已不再有树木生长,只剩下干黄的枯草。时间往正午移动,烈日呈指数加倍地炙烈,烤得登山客汗流浃背。曝晒在空气中的皮肤表面,水气瞬间蒸发,然而衣服底下的汗水只能不断涌生汇聚,乃至终于滴落时,就一路搔出痒乎乎、黏腻腻的轨迹,最后把前胸后背、双肩背带的痕迹全染得湿透。
午后天色变脸,温度骤降,浓雾顿起,顺着河谷蜿蜒,我们在潮湿的巨岩与溪水间曲折向下,这是一道长长仿佛来自侏罗纪的远古深壑。雾不断移入,从某些角度里只需抬头观望,就能见到雾气像被挤压吹出一般,从山顶喷射然后沉甸甸地坠落下来。在雾中,照明异样奇幻,雾让物体与景色的明暗对比降至低限,视线阴暗、却又发白。它隐蔽事物的方式就像夜色笼罩,令远处渐次退却,最终完全将之藏匿到里头。风景在天光不明中极度魔性,盘根错节的山树,挂满藤蔓与苔藓,在雾里的动态不怀好意,酝酿着诡魅,仿如受困诅咒的树妖,只在夜晚复活、扭曲起来,直到朝阳接触的刹那,妖们就凝结在动作的半途,那般鲜活而且毛骨悚然的形貌。

(山路 竹林)

(山路 血脉般的藤曼)

(山路 涉过小溪)

(山路 梯田正在准备中)

(山壁上的村子 向阳面)

(山壁上的村子 连牛马的人生都活在阶梯上)
白色越来越稠密,山雾正在丢失空气的特征,不再具备轻纱状而暧昧的阴柔特质,而凝结为具有质量的刚性。背景逐渐彻底消解成虚无,但雾还在堆积,它浓厚得不可穿透,简直如暴雪成堆,而至被自身重量压得严严实实,最后武断地把人的感官完全屏蔽起来。
山路从谷地穿出,前途通向一片留白,从后传来铜铃声,却仍不见系铃那头,一段时间后,才仿如浮雕显现于大理石那般,自雾中脱出了一头下工的白驴。终于摆脱重担的驴,满脸疲惫,踩着困乏的铃声慢慢踱步走来。白驴在白雾中看起来隐约如梦,浓雾为景象增添了悖离常理的童话色彩,使得这时候走来的无论是驴或珀伽索斯,都能引起心情的震动。

(山雾 一幅渲染的水墨画)

(山雾 从山顶降下)

(山雾 树林仿佛被幽灵占据)

(山雾 驴经过)
与夜
因为累又热,我们有时候爬着爬着,就会冒出些愚蠢至极的对话,比如J看见荞麦田的第一反应“这里一定有酿荞麦酒!”或无聊当有趣地钻研牛屎造型及制作的手法,甚至产生海市蜃楼的怪诞妄想,明明身在荒山野岭,两人却在认真讨论,“也许下一个村落会有法国bistro,我们就可以吃一顿好的!”“那我可以要一瓶隆河葡萄酒配个塔丁”……累到极处已丧失理智。

(荞麦田前的空地上 尼泊尔人正在重建学校)

(俯瞰荞麦田)
山上食物,多是尼泊尔传统餐食,例如最经典的手抓饭Dal Bhat,白饭+主菜+数样配菜+扁豆汤。每位厨子依照手边取材来烹调,人人的盘中飧,常是厨子刚刚从田里采回。住在韩国乡下的J父母,在自家小院里栽种些蕃茄、辣椒、生菜,J妈说,每天吃饭时,才去院子采摘,而那些蔬果日日成熟的数量,也许五根辣椒、四颗蕃茄、数株生菜,也很奇妙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好是三餐所需。我们见大妈拎着还附着土的高山菠菜,进厨房准备料理,不禁会心一笑。



(山屋风景)
幸运时,我们有肉,全是鸡肉。最好的是鸡肉咖哩,用山屋放养的鲜鸡烹制,首先辣椒蒜头咖哩等香料爆香褐化,整间食堂油烟大起,辛香弥漫,再将鸡皮煎至焦香发脆,最后再在自身鸡油里半炸半炖半晌,漫天肉香令饥火中烧的登山客心急如焚,端上桌香味四溢,放山鸡肉质结实弹牙,辛香料充分入味,微辣,油脂醇厚,风味浓郁。

(山屋料理Dal Bhat)

(山屋料理 喷式)
越近基地营,山区因为尼泊尔人的信仰,规定不可杀生,所以人人只能茹素,不过鲜蔬清甜爽脆,味道别致。最不济还有J私带入境的火腿罐头,然而味道惨绝人寰,像块穷极诡异的人工合成假肉糕,连山狗也不吃。爬到后来,这些山屋料理我们全吃到生厌,唯一能解馋的只剩辛拉面,如果再加个鸡蛋,可比人间至味。拉马知道我们嗜辣,常从厨房里偷渡几只本地炸辣椒,给我们加菜。
白天狂热,但一入夜气温马上掉至严寒,火炉实在太必需了,没有不行。炭火烧着后没多久,山屋各人便不约而同先来后到地围着它,与上方晾挂着的刚洗完的湿袜子、湿衣服、湿毛巾同堂并肩,喝茶看书取暖,无人介意。火炉真是种奇特的东西,具有引力一样的特质。
越接近基地营,物资越发珍贵,用火炉也开始要钱了,J说,有些山屋,连盖条被子也得付钱。山区里没网也没其他娱乐,所以通常睡得也早,晚饭后,最迟八点,登山客们早已就寝。

(山屋风景 谷地的河流在夕阳中像一条银线)

(山屋风景 破晓)

(山屋风景 最左是安纳普纳南峰 最右是鱼尾峰)
溪与雷声
随着海拔提升,温度越来越低。植相从绿意中,逐渐丢失颜色,大树先褪剩枯枝及寄生的苔藓、竹子、接着灌木林、最后只有地衣这种低等植物可勉强存活。
过了三千公尺,景色由灰转白,处处残冰。时值初春,山顶开始融雪,于是冰和着雪落下成为混浊的瀑布,击打途经的巨岩,冰水飞散迸裂,在山腰汇成汹涌的山溪,横扫席卷过小径,再万马奔腾地坠落深渊,加入谷底澎湃狂暴的灰泥色冰雪河,震耳欲聋的滔天爆炸声在整片山壁回响。有时没有桥,我们必须涉水而过,每踏出一步,都难以判断自己的下一步落脚处,河床里光亮亮的石头表面,究竟是流水还是薄冰。


(冰雪溪)
我们现在总算踏上基地营前的最后一段,过午即起的浓雾,此刻变成大雪,周遭转眼雪深及膝。刚开始我还满心欢喜地拍照,但不久后向导就忍不住催促前进,因为照眼前降雪的势头,很快前人的足迹就会被雪掩盖,我们将失去行道的指引。
山谷里一片白茫茫,降雪成了一种遮罩,遮蔽了视线,也吸收了声音,周遭除了雪砾轻巧而绵密地击打在地面与周身所发出的哒哒声、人们脚步迟滞沉重的簌簌声、高海拔(4000公尺)吃力上行的喘息声外,天地万物静谧如谜。忽然半空一团巨响哐当砸落,几乎令眼前及脚踩着的白幕与大地随之撼动。我立马被这枚声弹炸得原地跃起,直觉就是雪崩!雪崩!瞬间恐惧灭顶“我还不想死啊!现在就要向这个世界说再见,真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在一片白色大地当中,我不知道顶头山有多高,我不知道上面积的雪有多厚,我不知道如果灭顶可以往哪逃躲,最可怕的是,我也不知道如果被雪活埋了,自己的死状会有多凄惨。我只能借着反覆默念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让心里有一丝踏实。人类在大自然力量前,多无计可施、无力抵抗、无关痛痒。
待巨响停歇,向导见我们两人已被吓得六神无主,一个冲向路边跌进坑里,一个扑倒在地形同吃土,急忙趋前召唤收惊“别怕,只是打雷!”打雷?我半信半疑,稍松了一口气,心头却依然缭绕着那面半倒的标示牌影像『前方雪崩危险区』,心中不安不减反增。“若在加德满都,那是雨伴雷,至于山上,则是雪伴雷。”拉马淡定表示。然而雷声却不停,每一下都轰得我心惊肉跳,谁能确保这高山雷声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呢。
忽然大雪中一抹光芒从空中劈下,打在远远的巨石上,登时冰雪散裂四溅,正是我们早先走过的来时路。居然是道雷劈。这下连拉马也寒毛全竖,那真是我一生中最直面死亡的时分,此刻根本来不及挂念、遗憾什么,只有满脑子对眼下进退维谷处境的万分惶恐——“好端端活得不耐烦,跑来这座什么鬼山上”——怨气与恐惧直冲云端,天公也仿佛听见了这个心声,于是又一阵密密麻麻的漫天响雷。路途过半,我们现在是过江卒,只能进不能退。

(水流湍急)

(涉溪而过)
雷声间歇,硬着头皮继续,两小时后,总算在风雪中看见远远针尖般的小蓝顶,就是安纳普纳基地营。目的地现身让我重燃希望,于是快马加鞭地抡起脚步,用剩余的最后意志,在雪中卯起来向前冲。这时远远的有只山狗下山来迎接,向来客友善地打招呼,在我和J的脚边钻来钻去,结果我却跌到洞里,山狗见状赶紧凑过鼻子和身体蹭人,好像想扶来客起身。然而不知为何,向导却一直引得它不断吠叫,山谷这下狗吠四闻,再度引起我的紧张。后来得知,他们不是在玩,而是那狗特别恨他,见腿便咬,拉马只好一直捡石头打狗……
总算,经历数天,又是大雪、又是打雷、又是狗吠,鸡飞狗跳的一行人终于在雪中看见了“欢迎来到安娜普纳基地营”,这块牌子令人心中浮现了劫后余生的感动,互相拥抱道贺,拉马则为我们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刻照相留念。我与J才刚刚站定,山狗马上从被石头打跑的远方冲过来,打个滚便趴倒在画面前面,满脸良善相、乖乖巧巧双手交叠的合照,完全看不出刚刚还在凶神恶煞咬人腿,实在堪称喜马拉雅灵犬。
雪地里的高山的夜
登上基地营,J与我的首件要事不是休息也不是大吃而是先干一杯。这一路上,他的背包里始终暗藏一瓶来自马祖东引的高粱酒,就为这难能可贵的当下而庆祝。开瓶后,我们先不急着喝,两人不约而同,端着第一注酒又走回雪地。

(U型谷地中的草原与溪水)

(山顶落下的冰雪堆积成白色三角形的洲)

(景物开始覆上白雪)

(午餐时间 先去中途的山屋充饥)

(开始降下大雪)

(我们与山狗欢乐合照)

(安纳普纳基地营就在巨山脚下)

(安纳普纳南峰在我们照完相后很快藏进了云雾)

(登上基地营)

(基地营正面就是鱼尾峰)

(基地营旁的冰河谷壁)

(俯瞰)
对我们而言,登山之迷人,不在乎拓荒与冒险,而是它在各种方面,展现出一种极端的朴素。在山上,无论阶级、无论富穷,人人平等,每人的基地营都同样遥远,每人的夜晚也同样酷寒,山屋都一样破,料理都一样烂,没有差别待遇。在山上,剥去了社会赋予人的外在价值,我们都只是血肉之躯,承载着想继续向前的意志,单纯而简单,这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朴素。更甚者,从山的角度来看,究竟是一期一会的登山客、生于斯长于斯的尼泊尔居民、杜鹃花、鸽子屎,其实此间并无太大差别,只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心,很少有那样的时刻,能感受到自己的小,以及体会到“我”和其他人类与万物之间的酷似。
夜里,白天的暴风雪像一场闹剧散去,山头云雾全开、风轻云淡,周围雪地万籁俱寂。黑暗中安静而恬然,即使没有月光,满天星光也可以照明,白色起伏的山坡隐隐约约,如同一块巨幅的刻蚀银版照片。
深邃的星空无比晴朗,我想起妈妈还说,山顶的夜,繁星就像是贴在脸上一样,那么大、那么近。原来真是这样。
==========================================================================
微信公众账号:“寻找旅行家”,每天为你精选一篇有见地的独家专栏文章,欢迎关注,互动有奖^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