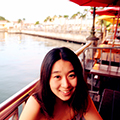我会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写作到末日
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的人都挺颓。昨晚我和我在加拿大的哥们——我们不算发小,但也算是认识较早,并且父母家都是北京西边军队大院的——聊完天,打算喝瓶酒,这才想起来家里的红酒喝完了,啤酒也喝完了,什么酒都没有。我这才想起来打电话的时候,哥们说他该一边喝着烈酒一边打,我还玩笑说别酗酒,他说有点。他在电话里提到这几个月想自杀,吓得我赶紧安抚他,希望他去看看心理医生,有空的时候安排一次国内旅行。
我这个朋友是那种很理性的人,这理性也让他移民加拿大后迅速完成了学业并且找到了工作。生活上他也迅速结婚生了子。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理性,他是凡事都以他人的要求为先,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人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们这些人的毛病估计就是概念太多,抽象理论太多,真是忘了自己是谁了。我们的审美害了我们。
“你的书里也没写你怎么好起来的,但确实就好起来了。”他在电话里说道。
我沉吟了一下:“确实没写怎么好起来的。”
“我理解里可能就是你重新获得了自己时间的掌控权。”
“可能是吧,这样我就可以想去哪去哪,不用把自己像钉子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样谁都会绝望的。”
第一天

我和B是在一座挪威的小城相遇的。十几年前,我们刚二十出头,后来我们分开了,绝交了,再也不来往。后来有天我们恢复了联系,他约我重返挪威,再一起逛逛。我同意了,这个念头听起来挺浪漫的。
我们约在奥斯陆。那天我们的飞机只相差一个半小时到达奥斯陆国际机场。我的飞机晚点,我没多等,就在机场的行李提取处见到了他。
这是十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你没怎么变。”他说。“你也没什么变化。”我说。
我们只在奥斯陆呆了两个晚上,没时间再去那座小城。奥斯陆比我们之前来得要脏一点,或许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春天了,草地上积雪仍在。在海边,我后来认识的在奥斯陆生活的朋友C陪着我们,给我们拍了几张合影。

C在海边的时候,曾跟我说起过去的一段感情。她说你知道那种看着空气一下子从蓝色变成灰色的感觉吗?似乎连空气密度都不一样了。
那怎么办呢?我想。或者应该复制那种情感,让空气再慢慢变回来。
第二天

头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约前男友见面。自从他结婚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的婚礼是我见过最棒的,从他给我发来的邮件照片上看,那个女孩的样子就应该是我。应该是我跟他一起办这个结婚才是。他隔着一条街,正在等过马路来找我,身边是个亚裔,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女朋友。在梦里,模糊了真实生活,梦里的我们都还没结婚。直到他们慢慢走过来,我才发现那是个男孩,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我去Potsdam找他。这是座离柏林不远的小城。以前我们在一起时,每个夏天他都会带我回父母家。我们在他家的苹果树上摘苹果,到邻居家的游泳池里偷偷游泳,在周围骑自行车,躺在草地上看星星。

没错,我们都没办法在这座小城生活,不过我可以去找他,再去一次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一天时间总够了吧?
第三天

最后一天,该去哪里?是应该静静呆在家里,还是应该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抑或去一个影响了自己世界观价值观的地方,找一个地标,自己呆一会?或者办个party,把亲朋好友哪怕是敌人都邀请来热闹一场,就跟李敖临死前的邀请函一样,约大家做个告别?我左思右想,哪一种似乎都不够完美,哪一种似乎都不是我真正所要。
《人工智能》里的机器人小男孩David等待了两千年只为了重返回童年一天,只为了和他的妈妈再共同生活一天,他听到妈妈说”I loveyou”就心满意足了。这电影的确是巨蟹座导演拍的,永恒的母爱与童年是巨蟹座内心难以磨灭的追求。就像《野草莓》,另一个巨蟹座导演伯格曼,片子里始终在回忆和回顾童年时生活的庄园别墅,童年时的初恋女孩,对时光的追忆……
我想好了,最后一天的上午,我要去柏林郊区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去看望埋在那里的猫Vanunu和克罗娜;下午,我在家里静静地读读我喜欢的书,晚一点,去纽约的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YPL),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曾在那里借过书和盘,它对读者非常友好,没有任何繁复的手续,只需要出示一个你在纽约的住址即可。我会带着电脑,在那里继续写作。即使明天就是末日,我也该把今天想写的文字写出来。

==========================================================================
微信公众账号:“寻找旅行家”,每天为你精选一篇有见地的独家专栏文章,欢迎关注,互动有奖^_^

上一篇:在巴黎一个人的时光(下)
下一篇:迷失在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