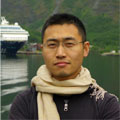清水到清水,到底要多久?
《D级旅途》系列,其中的D=Depth,这段旅途的不同之处在于——通篇只有一枚“旅途纪念手信”,旨在聚焦旅途“战利品”,探究“老物件”背后的故事。

(蔡科元作品,科元艺术中心收藏)
对于短途旅行,很多人喜欢问的问题,不外乎就是“吃喝、住宿、猎奇”这几样东西。
大致来说,如果刚刚讲的几个大项,不能构成满足的想像力时,通常都会放弃。
讲起来,似乎也没什么错。
毕竟到一个“吃喝、住宿、猎奇”都不及格的地方去玩耍,浪费时间在平淡的目的地上,人生苦短,何必呢?
说什么也没有理由让步吧!
不过,我倒没这么严格。
一般来说,我都是碰到什么了,才去那个什么地方。
或者,另外一种自主性的,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如果是这个,根本连偶然都称不上,就是突然的外出,坐上车,又毫无理由地下了车,所谓“途中下车”这样的人。
饭田先生是去年在静冈乡认识的长辈。
当时,因为急需了解水源与茶园的相互关系,由东京方面的熟人介绍后,由于状况急迫,没办法先打电话或请介绍人事先联系,就直接坐班次最近的快车抵达。
他在清水车站月台,远远的就跟我招手,像久别的亲戚或熟人那样的表情。
真是意外,固然下车的人群并不算多,不过,他居然可以一眼就辨识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办到的?
更讶异的是,他居然可以使用若干台湾话在某些语助词里。
我们沿着整齐的梯田茶园,一层一层向上缓步,很快地,这位(绰号)耕太郎就带着我走到高地,往港口眺望的同时,问了几次“到过清水没有?”
“这是头一次,除了讶异茶园修整得跟盆栽没有两样之外,我其实更期待这边的浦烧鳗鱼饭,这里的稻子长年有洁净的水源滋养,据说即使冷饭也甜美得很。”
“鳗鱼饭好吃的因素,其实很简单,活动量大的鲜鳗、蒸煮略干的米饭,还有烤肉时刷上的酱。这三要素,这一带,即使是无名的食堂,都有这种本事。”
他继续眺望远方,好像穿过什么障蔽的透视。
丰富透顶的茶园渐层的绿意,向青蓝晶莹的海水延伸过去,尤其是色块密接处,波浪的白色碎沫时而让绿比率多一点,或让青的比率少一点,这种视野,只能用难以言喻来表达。至少我没在其他地方见识过。
“我说的是台湾的清水,Kiyomizu。这里虽然也叫清水,不过念成Shimizu。”他从外套拿出掌型手帐,端正地写给我看。
我摇摇头,表示从没去过,即使离自己住处才两个钟头时间的这个小镇。
事情办完后,我们上了东海道高速铁路,在浜松新站下了车。拐进一条容易被忽略的巷子里。
鳗鱼饭店,叫Atsumi,是间整理过的五代老食堂,since1907。
不过,我对几代或百年这种事情兴趣几乎等于零,好吃的现况可能比什么都要重要。
跟随饭田先生的意见,我们都点了基本款的两段式鳗鱼饭。等候烤鱼的时间,他问我要不要试试白烧的,配纯米冷酒很搭。
鳗鱼饭一下子就干净见底,连细针般的鱼刺都烤酥,确实很不容易。
白烧鳗蘸了海盐,咀嚼第一口的同时,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忙。
“年轻时,我在台湾Kiyomizu待到快四十岁,遣送返回这里的Shimizu老家时,反而觉得台中清水才是我的家乡,这样子过了几十年。看到你的时候,我确定是该去看一次的最后时刻了。”
他又叫了两合冷酒。
我答应,会陪他逛完他想去的每个清水角落。
就这样,雨季期间,我在从来没来过的清水火车站下了车。
站里的乘客少得像尽责的临时演员,倒凹式的候车室内,很有味道的居中排了两支实木长条椅。
时间好像还真在1930年代。
打开耕太郎的掌型手帐首页:“下车时,完全感受不到去年地震的痕迹,暖色的长条贴砖和洗石子的柱子,竟让我这个异乡人有了确定感。”
他把当年的笔记影印缩小贴在页面,提示要与年轻初次的工作地点重逢的记号,真不简单。
严格说起来,这算是本建筑侦探笔记吧?
在夜雨午夜还没打烊的夜市,街角旧式旅馆小书桌上,边翻阅边查看散步路径。
这栋还提供热水瓶的老楼层,就像小学毕业旅行的记忆,空间狭窄、低矮却洁净。
打开窗探望微湿的街,还有奋斗拚宵夜的本地人群。
饭田笔记之外的,唯一算是自己的部份,可能就是吃碗清晨七点多出菜,午前就结束的“荣米糕”。
清水一直以这种糯米饭为名。不过,外人提起的十几家店铺,这家这里人才吃的早午餐,多半被忽略。
虽然都是以木工改行的王塔为宗师。
住在这罕见早市、夜市同街的唯一理由,就是“荣米糕”就在旅馆隔壁,说起来,真是爱吃到无所不用其极了。
除了渗入肉片汁液的糯米饭的滑嫩惊奇之外,更难解的是淋在饭上的红酱,说是用在来米和红椒研磨的,据说剂量的控制,完全靠目测。
连点来的卤蛋,炖豆腐,都是这种颜色,只能说相当奇特,要不然呢?
往街心走去,市场由一间木结构的八角楼在十字路展开,对角叫“金足成”的银楼匾额喜气洋洋的用肥肥的颜体字署名“小东山”这样不像书法家的作者名,下面一条横春联:“金融充足万商成”。
这两间,都在饭田先生的纪事里。
这条市场,算起来,从夜市到早市,中间静止的休息,算算仅四个钟头左右,
接下来,流连在有几十种鲜果蜜饯摊,买了传统梅子粉后,迷了一小段路。
乱窜的到了另一个小市集,路上发现不少眼科招牌,几乎到了抬头就是的地步,吓得我只好平视直行前进。
转角平淡无奇药妆店,发现二楼有个展出以“既视感”(我自己想的,因为作品都充满了Déjà vu的梦中滋味)为主的画廊,名字叫“科元”,为什么呢?
少女般笑咪咪的企划人员给我看了一件高不到四十公分的木雕刻斗鸡,说是民国前四年生的蔡科元木艺家手雕作品,他是画廊主人的长辈。
不过,这件作品让我很讶异。
仿佛等待上场的这只,安静的眼神、蓄势待发的片片羽翼,用强健的脚攀在小山一般的石块上,即使只是干净单纯的木头色泽,但,几乎马上要动作起来的样子,很难想像只是一般木刻匠人的作品。
另外,巧合的是,来到这里的耕太郎当时十五岁,大了蔡先生三岁,他们在这小镇相遇了吗?
我多住了几天。把本子记载的光复街闽清和折衷式洋楼、光明路上洋式商店集合屋、清水街的连栋长屋、依然有“印书馆”的文昌街、甚至走上去费力的神社石狮子等日据时代的建筑相关照片都拍下来,寄给他。
附上的说明是:“连我都惊讶,记事本里的每一间,居然都好好地存在着。”
==========================================================================
微信公众账号:“寻找旅行家”,每天为你精选一篇有见地的独家专栏文章,欢迎关注,互动有奖^_^